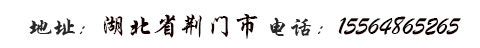感时花贱酹
|
清明回乡,到处都是花。 屋前屋后,自然是桃花红杏花白,稍远处则李花疏零樱花团簇。河边岸上,则杨柳扶摇,蒿菜渐白,零星的花儿随处点缀着。望眼山坡上,嫩绿和枯萎间杂和共存的茅草丛和刺篷里,最醒目着一丛丛的桎木,肆意地绽放红色和白色的花儿,十分的应时应景也应情。最不解人意的要数紫云英,大片大片地铺陈,体态娇柔,花色艳紫,含露欲滴。风儿一过,它们还自顾自惬意地来上一场集体轻摇舞,全然不管上山的人和山上的人,让眼睛想躲也躲不过它。它们美丽着,我却没有心情。 这些花儿,我看在眼里,却不是我的关心。 我有一个阳台,阳台上有些花儿。说是花儿,却也只是一种统称而已,真正能绽放的却是没有几种。对那些不开花的花儿,我却有些喜欢,至少有点关心。 我不太敢养名贵的花草,一是因为它们太有价值,二是因为我懒且无知。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——因为爱他们,因此不愿意去毁了它们。 于是,我的阳台上有绿油油的虎耳草,闷闷地匍匐着,贴着墙角。细细去看,叶面边缘毛茸茸的白须诉说着它低调的温柔,不为人察觉,也不愿为人察觉。那盆多肉类的玉树,名字确实有点华丽,我却更愿意叫它“落地生根”,这是民间的叫法,更有地气些。很多事物都如此:一旦书面化或是所谓的“正式化”,便远离了某些本质,也不再那么可爱。就像玉树,也叫“落地生根”,我儿子小时候还把它叫做“打不死”和“厚脸皮”,因为他做过实验,随意掰下厚厚的一片随手一丢,它自可以成活,低贱但活了。吊兰也是属于比较“贱”的那一种,除了浇点水,便可以不管它。它只管自己去垂吊着,偶尔有一处可以歇歇脚,它的再生根便冒了出来,在某个节点处嫩嫩的弱弱的,偏又能抓住些土就驻足了。 渐渐的,我的阳台上都是一些比较“贱”的花儿了。我想这样也好。 虎耳草 玉树 吊兰 也有例外,有朋友搞来两盆野生的铁皮石斛。这颇让我紧张不少。于是我查找资料,拜访高人,细心打理,结果却也简单,养花高手们告诉我养铁皮石斛的三大绝招:一是光照合适;二是一定要用松树皮培土;三是只要浇水,且不要乱换水源。尽管就这么简单,我还是惴惴不安。去年,铁皮石斛开了花,黄黄的花瓣,蓝蓝的花蕊,柔柔的却不孱弱,娇娇的却不腻人,安安静静的,真好。于是我也就更加珍爱它了。今年春天,工作一调动,心里对它们也有了些牵挂。牵挂于它们对环境要求的很简单。可就是这种近乎于“一元”的简单最让我有点揪心。世界早已太多元,“一元”已成奢侈。 此刻,我有了新的发现:我不敢养那些开花的花儿,其实是害怕他们的凋零和凋谢。我害怕,害怕它们的凋零和凋谢是因为我。 铁皮石斛 阳台上,还有那两盆盆栽,又有些许的不同。 一盆是紫薇,一盆是银杏。都根粗如瘤,矫枝如虬。朋友送来时,它们都活的恣肆野蛮,我却有些担心。担心一个小小的花盆怎么能有足够的土壤任其攫取养分,也担心类似于“病梅”的矫饰会伤害了它们。于是我自作主张地找来一些苔藓,铺叠于土上,为的只是想护住营养和水分。盛夏十分,紫薇碎碎的花儿开满了一树,像极了紫色的满天星。银杏树上尽管树叶稀疏,到了秋天也善解人意地奉献了金黄,我的心也很是疏朗和惬意。哪曾想,秋未尽冬未央的时候,它们就枯了,不声不响。待到寒冬,它们默默地,默默地死了。默默地,它们死了。伴随他们死去的,还有一株小叶黄杨,就是我儿子称为“千年矮”的那种。于是我开始恨自己,恨自己的贪婪:紫薇和银杏,原本高贵,我却偏偏要去养它们。我深深地自责,是我的贪婪害了它们!更为难过的是,连那贱得不能再贱的苔藓也被我养死了,它们惨白如枯槁,干瘪在树下,仿佛没有安葬的逝者。 在那份自责中,我执拗出一种不甘。始终不愿意将这三盆盆栽彻底清除,每次还是顽固地去松土、浇水。进入初春,有一些野草居然冒出,依然是些低贱的类似于稗草、狗尾巴、鹅恋草、老鼠根、金钱草、蒲公英之类的野草,摇曳在盆中。调离怀化后,每次回来,我还是坚持给这三盆枯死的盆栽松松土、浇浇水,由此还给它们掺和了一些榨过油之后的茶枯粉。我知道,做这些没有什么用处,我只是在和自己较劲。其实,我连等待它们复苏的希望都没有。我清醒地知道——它们死了。但我还是告诉学业繁重的读高三的儿子:每周必须给它们浇水。 我知道这是浪费,但我犟卵般地一根筋地坚持——浪费,就是生命进行时。拔掉,才是过去时,过去完成时。 紫薇 银杏 小叶黄杨 谈不上什么惊喜,这次清明节从老家的山上回来,我依然去给我的那些花儿浇水。紫薇和银杏居然爆出了新芽。它们,活了! 它们活了。我固然开心。但是我也不会去放大,不会去关联。不会去放大它们活过来有什么伟大的意义,也不会将它们的复活与我的付出关联起来。更不会去自以为是地强化是自己在拯救它们,然后渲染出“不放弃、不抛弃”的初中生作文的主题主旨。至少,我还不能无视那株依然没有复活的小叶黄杨,这株“千年矮”已经注定变成了“万年枯”,且不一定能“枯万年”。桃花红杏花白,终都将缤纷,紫云英最终也将被翻耕化作土肥,那都是一季的绚丽。渐渐地以为,它们都有他们的花期,它们也都有它们的生命。我自推卸责任的以为:活着、死去、复活,都不由我。活着,是因为它的“贱”;复活,是因为它更“贱”。 贱,有时是一种选择,是一种能力,也是一种情怀。有时我更愿意相信是一种无知和无奈,是一种“不得不”。有些花儿,因贱而在,因贱而活、而复活。 渐渐明白:花开花谢,或活或死,我参不参与,它自那般。在它和我之外,还有很多很多的力量。尤其是那些不为我们所察觉和感知的力量,例如“贱”。土壤之贱,加之花儿自贱,它们更能摧枯拉朽,也更能润物无声,还能涅槃重生。在我们的感知和认知之外,定有另外一些力量。它们分明存在,还作用于我们,只是我们不知道。 由此,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: 即便我们只想做好自己,只想做自己,也难。 —04—04清明 斤多尼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ercaoa.com/heczz/373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爸爸的小花坛
- 下一篇文章: 小欧科普时间,也许你从未见过的奇花异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