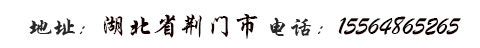我从山中来,带回虎耳草
|
点击蓝字,邂逅美好 去年往菖蒲园看菖蒲时,无意中在一旁的田埂上发现了成片的虎耳草。厚实的圆叶上,刻画着清晰的叶脉,布满毛茸茸的细毛,格外惹人注目。 虽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虎耳草,但之前在读沈从文先生的《边城》时,便充满好感,并一直好奇到底是什么植物,可惜从未主动去查过。后来读到柳宗民先生在《杂草记》中对虎耳草花姿的描述时,更加“心向往之”。没想到,却在这幽幽山谷里遇到了。虽恨相逢甚晚,却如“异乡逢故知”,倍感亲切,当即便擅自决定挖一些“请回家中”。 虎耳草和水芹、鱼腥草纠缠在一起,好在根不深,不费吹灰之力就挖了出来。但叶子十分脆弱,携回途中不小心碰破了几枚,只好忍痛剪掉,栽在了树荫下石头旁的花盆里。翌日浇水时,发现根部已稳定,叶子也恢复了精神,看来已经适应“新家”。 自此之后,我便“一日看三回”,意外发现虎耳草的生长过程很有意思。红紫色的匍匐茎从叶腋间不断伸出,像是触角般试探外面的环境,一旦着地,顶端上就会长出一株株子辈虎耳草来,然后接着生长。浑然不觉间,花盆旁的石头缝里便都布满了虎耳草。 今年4月下旬,每株虎耳草的根部中央各自开始长出一根长长的红茎,小小的分枝上顶着一只只花苞。几天后,随着茎越长越高,分枝也开始延展,花苞愈加分明。 又过一周后,花苞终于接连绽放。上面的三瓣最先露出,下面两大瓣起初蜷曲,但像蝉蜕壳时的翅膀一般,很快就全都伸展开,犹如一个个“大”字挂在枝头,模样十分独特。 《杂草记》对花姿描写贴切详细: 花瓣五片,下面两片比较长,好似伸长的双腿;上面三片就非常小了,凑近观察,白色花瓣上缀着几个红点,特别精巧。雄蕊呈放射状,比小小的花瓣还长,是再好不过的点缀。花朵虽小,形状却独特,让人过目不忘。望过去就像穿着白色裤裙翩翩起舞的舞者,分外可爱,并不整齐的花梗,反而让它越发轻盈纤巧。 捧书对花比观,确实如其所言。一朵朵轻盈的花朵犹如白色的鸟儿,风静时停于枝头,风起时微微摇晃,凝望时赏心悦目,让人陶醉。 虎耳草在日语中叫ユキノシタ,写法有两种。一作“雪之舌”,侧重花,即指下方两枚花瓣犹如雪的舌头,雪花有无舌头不知,但形状确实像舌;一作“雪之下”,侧重叶,虎耳草为常绿植物,经冬不凋,银装素裹之时,虎耳草依旧青青如我,青白分明的画面不难想象。 顺便一提,虎耳草的叶子据说还能拿来做天妇罗。前几天我摘了几片,裹上面糊过油炸熟后,叶子依旧青翠,吃在口中也是毛茸茸的,味道有一股青气,还算可口。 关于虎耳草的命名,日本植物学界有争议,国内也是有各种“昵称”。《本草纲目》云:“虎耳,生阴湿处,人亦栽于石上。茎高五六寸,有细毛,一茎一叶,如荷叶盖状,人呼为石荷叶,状似初生小荷叶及虎之耳形。” 石荷叶是从叶形命名的,较文雅,其他还有金钱荷叶、金线吊芙蓉等称法,但也有像耳朵红、猫耳朵、狮子草、猪耳草、蟹壳草、佛耳草等较朴素的名字。更有着眼于红色匍匐茎而命名的,如红线草、丝丝草、红丝络、红线绳、丝绵吊梅等。侧重不同,足见人们对其“爱之深”。 不管花还是叶,皆招人欢喜。除此之外,虎耳草还是种药草,具有清热凉血、消肿解毒的作用,能够治疗风疹、中耳炎、冻疮、湿疹等。不但作用大,还适应各种土质,尤其爱长在对其他植物来说难以存活的石块上或石缝里。虎耳草的学名“saxifragestolonifera”中的saxifrage一词,就有打破石块的意思。这点朴实与谦卑,也深受沈从文先生欣赏。 虎耳草花语有好感、恋意、深爱、博爱,无不与感情有关。《边城》里,翠翠撷了把虎耳草,将内心的情绪寄予其中,如今在东瀛邂逅,想起那懵懵懂懂的青涩感情,更觉虎耳草愈发惹人怜爱。 龙猫的国度究竟什么模样? 敬请持续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ercaoa.com/hecyy/950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靳彝甫汪曾祺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