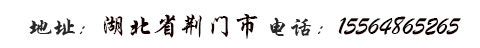文化周刊读书丨书林间的遐思读时光
| 阅读的状态有多种,有人读而不著不评,只为愉悦心性;有人喜欢边读边教,输入输出两不误;也有人只为炫耀,以此哗众逞口舌之能。还有一种人,既读又写,这类又可粗分为两小类:一小类是读专业书,精进后著学术作品;另一小类则是读书广杂,将思考后的感悟提炼与众分享。张宗子应属于最后这一类。《时光的忧伤:张宗子自选集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8月出版)是他三十年散文作品的集结,收录了《黑鸟的翅膀》《乔伊斯的雪》《叶芝》《时间的比喻》《秋天的湖》等五十余篇作品。主要内容涉及沈从文、叶芝、乔伊斯、梵高等中外著名作家、艺术家以及作者对生活、艺术、理想等思考的散文;涉及作者在北京、纽约等地生活的叙事和回忆性散文;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内容的随笔性散文。其中既有阅读感悟,也有生活体验;既有抒情、叙事性散文,也有读书随笔;还有一组以植物,尤其是文学艺术中的植物为主题的散文。文章语言平实典雅,遣词造句独具匠心,沉静中不失华彩,文字间有着明显的时代气息和读书人的性格烙印。“沈从文的气质像李商隐,是颇为伤感的人。”作者写道,“贯穿在他作品里的愁绪,从他文学起步时的习作,直到晚年的书信,基本不变。早年,他的哀愁中萦绕不去的是思;晚年,则是看透世事后的愤惋。他性情温和,但不豁达。他的隐忍是靠坚强的毅力支撑下去的。”这是张宗子通过作品、人生经历对沈从文先生的慨叹、评定,虽是一己之见,却能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。走进沈氏故居,沧桑之感顿生,这篇《沈从文的忧伤》继续写道:“从这里你便知道所谓沧桑,是柔软的,是屈服和顺从的那种柔软,就算有不平郁结于内,也被沉积的时光掩埋了。”很多读者因作品喜欢作者,甚至想走进其内心世界,于是当面求教、阅读传记、寻访故居,无论怎样,所绘“肖像”接近大众“印象”就好。在《虎耳草》中,作者引汪曾祺旧文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说,沈从文家养了一盆虎耳草,很多访客不识。虎耳草是沈从文在湘西古城留下的童年记忆,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,是沈从文去世后其夫人张兆和“栽在墓碑石下”的思念。情深至此,作者意味深长地说:“人把理想和情感寄托于世上的微小事物,这事物因此从自然中超脱出来,进入人类的文化和审美世界。自古及今我们的文化史中相当的一部分,就是由这些我们敬爱的人物将个人的美好情感客观化而留下来的。心有灵犀的异代读者,从此得到滋养,丰富自己的心灵。这些花花草草,与无数其他的细节一起,构成我们的精神故乡。孔子的幽兰,屈原的蕙草,陶潜的菊花,苏东坡的海棠,无不如此。”作者对外国文学与艺术也有所涉猎。在《黑鸟的翅膀》中,张宗子提到法国钢琴家格里莫的色彩感。在格里莫的心中,每个单一的音符都和特定的色彩对应,“在她凭记忆弹奏时,她记起的不仅是音符,还有颜色的印象”。张宗子认为,在艺术和艺术欣赏里,迷恋常常表现为一种很高的趣味。“颜色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对比中显示出美的,也和质地密不可分。我没有特定的迷恋,喜欢单纯,包括艳丽的单纯,也喜欢繁复。蓝色和相近的淡紫色及灰色,使我觉得特别舒服,大概是因为它们安静和纯洁,还带一点梦幻的性质。我偏爱的作品多半是优雅和内敛的,态度雍容平和,不咄咄逼人,富有想象力,没有任何羁绊,自然体现了人在精神上的无比轻盈和自由。”在《乔伊斯的雪》中,他认为,英国作家乔伊斯的短篇小说《死者》被约翰·休斯顿拍成电影是失败的。影片对细节的处理(如旅馆中不开灯的场面)缺失应有的氛围。“为什么不要开灯?对比小说绝大部分篇幅的欢笑嬉闹的宴会场面,旅馆的两人世界是幽静的。正是在幽暗中,加布里埃尔得以沉浸在安睡中的格丽塔的心灵之中……应该说,死亡和爱息息相关,因为爱许诺了生死,同时超越了生死。而在约翰·休斯顿的电影里,所有这些都没有。”作者笔下所描写的景和物、人和世界、人和生活的关系,都在润物细无声中,投射出一种平静、安适的超然。书中多处流露出作者既独享孤寂,又希望为世道人心秉笔而歌的努力。王松林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ercaoa.com/heckh/1361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无尽夏已悄悄谢幕,圆锥绣球登场诺可爱养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