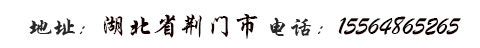记忆我的草房子
|
写在文前:今天,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,父亲节,本想写一写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教育性,但因事外出晚归,便用了这篇旧文章来回忆一下那些过去了的旧时光,回忆一下爸妈年轻时的那些岁月…… 本文写于年5月,那时,四班娃即将毕业,他们写自己的童年时光,勾起了我的思绪。他们对于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是极感兴趣的,于是,我也拿起了笔…… 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晚上,我总会想念我的草房子,心底便会漾起一股莫名的悸动,一种莫名的惆怅…… 草房子有多大年龄,我不知道,只知道奶奶年轻的时候,从宗族老院那边搬过来时就修建了。那是用泥土夯的墙,麦秆盖的顶,老鼠和蜜蜂在土墙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窟窿。墙角还生活着一种生物---“地牯牛”(一种很小的软体的扁扁的小东西,我们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学名是什么,大人们就这么叫的)。这里,装着我儿时的美好记忆。 草房子的顶,每年会翻新一次。麦秆是梳理过的。把钉耙齿朝上绑在高高的长凳上,一把一把地将新收的麦秆放到钉耙齿上梳,麦秆上的杂物就被钯齿留下了,就像过滤一样。梳理过的麦秆,秆壮色黄。然后就打成一捆一捆地往房顶上抛。我们几姊妹都会抢着做这些事,感觉挺好玩的。不过,大人们总会嫌弃我们,说我们力气小了,扔不到位。也是的,爸爸他们在下面扔,房顶的人接,简直就是一扔一个准。房顶上的人,将接到的麦秆分散到需要铺的空地方。房顶上,原来的旧麦秆,已经被清理下来做柴烧,只剩下一根根作房梁的竹竿。巧手的匠人们动作娴熟地将捆好的麦秆解开,均匀地铺展开来,然后用一个木板做的工具拍拍,压压,让铺好的麦秆整齐,密实。就这样一层压一层,新的房顶就出现了。我的大姑父和一个远房的二叔盖房手艺远近闻名,村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请他们盖的。现在,会这种手艺的人应该是没有了的吧--我觉得他们真可以去申请非遗了。可惜,大姑父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……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房顶没有及时翻新,或者遇到老鼠、鸟儿的破坏,房顶上就会出现窟窿。遇上下雨就会漏雨。那可真是大下大漏,小下小漏。家里大大小小的盆子全搬出来接雨了,整个屋子“叮咚”“滴答”的声音此起彼伏,就像在开音乐会。房间里湿漉漉的,睡觉也不安稳。灶房里更惨,生火做饭,柴烟排不出去,屋子里烟气腾腾,熏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屋顶的“阳尘水”(音,像酱油一般的脏东西,由于烟雾熏屋顶形成的)冷不防就滴下来,这儿几滴,那儿几滴,有时正好就落在煮熟的饭菜里或者衣服上。于是乎,煮好的饭菜赶紧用东西盖起来。我们呢,则戴上草帽或者套一件旧衣服在灶下烧火,时刻警惕着头顶上会掉下来的东西。我妈或者我姐,则戴着斗笠,穿上破旧的衣服,在灶上忙活着,活像一个唱大戏的。饭菜熟了,一家人围在饭桌上吃饭。不时会遭遇那东西掉一滴到饭里或者菜里,然后大叫一声,将那一块饭菜挑出来,大家笑笑又继续吃着。有时,那东西掉得厉害,我们就将饭桌搬到堂屋里去吃饭。 有一次,接连几天遇到暴雨,草房子漏雨太厉害了。一天晚上,睡梦中,只听“轰”的一声,灶房里的一堵墙倒了。半夜三更的,得防贼呢。于是,妈把我们叫起来,我们齐心合力地用一个木板将那堵墙挡了起来。虽然墙倒了一堵,不过我倒有点欢喜。因为我家后墙上没有后门,到草房子后面,得绕一大圈。现在好了,到屋后的小伙伴家,或者到屋后的菜园摘菜,一下就可以到。更重要的是,到后墙根方便多了。 草房子的后墙根,是我们的乐园,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。土墙上有许多蜜蜂的杰作--窟窿。我们拿着瓶子,捏着竹签,像侦察兵一样,眯缝着眼睛,搜寻窟窿里是否藏着蜜蜂。一旦有发现,便将竹签伸进去,轻轻地把里面那个小东西往外带。另一只手,则将瓶子对着窟窿口,只等洞中的家伙出来,就“请君入瓮”。有时,那“君”也不会乖乖入瓮的,在掏出来的那一瞬间,它振翅飞跑了,所有的努力泡汤,留下一声声后悔的叹息,接着,又开始下一个目标的搜寻。 掏出来的蜜蜂,都装到瓶子里。我已记不清这蜜蜂后来是怎么处置的了。但是,那在窟窿里掏蜜蜂的小心翼翼,掏到后的开心,蜜蜂逃飞后的怅然,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。 土墙根,有许多细细的泥土,那是“地牯牛”的杰作。在这些细细的泥土里找寻“地牯牛”,也是我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的游戏。我们或蹲或趴,一边用竹签刨土,一边不转眼地搜寻,嘴里还念念有词“地牯地牯牛牛……”。一有发现,便大叫着装进瓶子里,像找到珍宝似的向别人炫耀一番。 草房子的后面,是我家的菜园。里面种着各种应季蔬菜。每到做饭前,我们就会到菜园里摘想吃的菜。现摘现做,新鲜得很。每逢暑假,我就负责做一家人的晚饭。中午,大家在睡午觉,我则开始准备晚上的菜了。太阳虽烈,但是在豆角架、苦瓜架、黄瓜架、豇豆架下穿梭,一点儿也没有热的感觉,何况,菜园四周还有大树(我记得当时种的是大家叫的水冬瓜树)和竹林庇护。发现了长大的豆角、苦瓜、黄瓜,还有茄子、辣椒等等,就采摘到菜篮子里,一种收获感,充斥着整个身心,让人愉悦得很。这些菜,基本上是隔一天就会有新的长大。最常摘的要数空心菜了。一茬一茬地摘,这茬摘完,那茬又长出来了。每天好像都有这菜。我本来就最爱吃空心菜杆儿煎辣椒--粗纤维,呵呵,毕竟是牛,这菜适合牛的口味。苦瓜也用来煎着吃。暑假没事,我就研究做饭菜。我自创了一种新吃法,苦瓜煎好后,和锅贴一起炒,就像苦瓜熬肉那样香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肉,毕竟是个好东西。这也成了我最爱吃的菜--已经许久没吃这些菜了,写到这里,竟然“垂涎”了。现在,因为忙,自己下厨的时候太少太少,买菜的时候基本没有,这两道菜,已经被忙碌遗忘了,被长大遗忘了……有好多人,好多事,好多物,就是这样被遗忘的吧? 图片来源于网络 草房子的前院,种着几棵柿子树、柚子树。初夏的乡村之夜,空气清新,带着凉意,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柚花香。沐浴在吸不够的花香里,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浸透着花香。一簇簇白色的柚花挂在绿叶丛中,如羞涩的姑娘,犹抱琵琶半遮面;也似调皮的孩子从绿叶丛中探出头来,眨巴眨巴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好奇地张望着这可爱的世界……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。在柚子树下,搬一把椅子,静静地靠着椅背,斜躺着,望着星空天马行空地想象。然后在花香中,在蝉鸣蛙噪中,甜甜地进入梦乡……突然被劳作回来的爸妈叫醒,迷迷糊糊不知天亮还是天黑…… 进入九月,柚子渐渐成熟,我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享用柚子了。拿一根竹竿,看中哪一个柚子,就用竹竿顶住柚子底儿使劲地往上撑,几下子,柚子便跳到了地上。有时调皮了,胆子大了,也上树去摘。坐在树杈上,视线被枝叶挡住了,反倒没有地上那么能瞄准目标。坐了一会儿,不甘心地顺手摘一个,丢给下面的姐姐或者弟弟,“哧溜”下来了。 深秋时节,柿子红了。妈会把柿子收下来,用米糠掩起来。大约半个月的样子,柿子就被捂熟了。柿子太多,一时掩不了那么多,就留一些在树上。秋雨潇潇,那些熟透了的柿子会自己掉下来,这比用米糠捂熟的好吃的多--毕竟天然成熟的吧。这段时间,我们总会留意柿子树下。每天早晨,我们也会争着早起。草房子静静的,院子里静静的,一切都还没有醒来。深秋的清晨已经有点冷了。在蟋蟀的琴声中,总会在柿子树下拾得一两个战利品,满心欢喜地掩门继续睡去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 草房子旁边,有一口井。井水清凉,井壁有青苔,还生长着一种叫“虎耳草”的植物。涨水的季节,井水也会跟着涨。院子里几户人都在这里取水。我们有时会把从河里捉来的鱼放到井里养。井里有了鱼,我们也多了许多乐趣,经常会伏在井边看鱼。大人们看见了,总会把我们骂走,因为怕我们掉井里去。 不幸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。有一天,我和姐姐赶鹅回家,姐姐在后面赶,我在前面唤。我边唤边倒退着走,唤得起劲儿了,忘记了后面的井……“妹儿掉井里了!妹儿掉井里了!……”姐惊恐地喊着,而我,却在水中迅速下沉。至今,我都还记得在水中下沉的感觉:周围好静好静,我的心,也好静好静。我什么都听不见,什么都看不见。我,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世界太静了,只有我一个人。一种孤独感和恐惧感紧紧地攫住了我……后来的事情怎样,我不知道。只听说当时爸妈正在奶奶那边闲聊,听见姐姐的叫声,还以为是鹅掉井里了,飞快跑过来。见是我掉井里了,爸爸就赶紧下到井里把我给捞起来了……感谢爸给了我第二次生命……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现在已经人到中年,我时刻准备着迎接我的后福,也期待能将我的福,分享给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。 井的旁边,是别人家的土墙。上面也有窟窿。不,确切地说,那应该叫“洞”。那是一种叫“士雀”(音)的鸟的家。我们也喜欢去探寻它的家。拿着井竿(取井水时钩水桶的竹竿),往“士雀”的洞口一钩,井竿就挂住了。顺着井竿往上爬,就可以探得“士雀”的家。有一次,井竿没挂好,在往上爬的时候,我重重地仰面摔地上了,后脑勺生疼。还来不及喊疼,姐就把我扶到一边,一个劲儿地叫我别吱声。因为被爸妈看见了,一定会换来一顿打。于是,我便揉揉还在生疼的后脑勺,把快流出来的眼泪硬生生地逼回去。 光阴似箭,一晃就是四十多年。曾经,我是那么渴望走出我的草房子!可等到如今,草房子没了,爸妈老了,我们三姊妹也各自有了自己的新房子,我又那么怀念我的草房子!我怀念草房子里的煤油灯,草房子里的“阳尘”,怀念老房子里漏雨时一家人的忙成一团,怀念爸妈的温柔的表扬,怀念几姊妹的笑声,也怀念老房子的打骂声,哭喊声,求饶声,还有几姊妹的斗嘴声……我怀念老房子的一切一切。它们如同一团火,时时温暖着我的心;它们如同一盏灯,让我在人生路上,走得踏踏实实!它们也是我温暖的港湾,让我在受伤之时,在午夜梦回之时,不会感到孤单…… 啊,我的草房子! (本文写于年5月4日凌晨,待修改) “春春老师的阅读小屋” 长按下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ercaoa.com/heccf/977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长清科学middot科普常识教你
- 下一篇文章: 奇闻凌晨,山西一酒吧举行淫秽表演被查,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