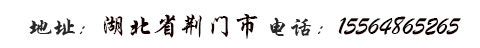名人堂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
|
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作者:汪曾祺 沈从文简介: 沈从文(-),男,原名沈岳焕。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,撰写出版了《边城》等小说。 年-年在青岛大学任教,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,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。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,著有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 年病逝于北京,享年86岁。 正文 沈先生逝世后,傅汉斯、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。字是晋人小楷,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。词想必也是她拟的。只有四句: 不折不从;亦慈亦让; 星斗其文;赤子其人。这是嵌字格,但是非常贴切,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。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。他在填履历表时,“民族”一栏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,可以由他自由选择。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,狠劲,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。他少年当兵,漂泊转徙,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。吃的东西,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(煮在豆芽菜汤里)。行军、拉船,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。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,举目无亲。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,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。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“消化消化”而发愁。冬天屋里生不起火,用被子围起来,还是不停地写。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。他真的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。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,竟成了一个大作家,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,真是一个奇迹。 沈先生很爱用:“耐烦”二字。他说自己不是天才(他应当算是个天才),只是耐烦。他的“耐烦”,意思就是换而不舍,不怕费劲。一个时期,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,每年都要出几本书,被称为“多产作家”,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,从来不是一挥而就。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。他常流鼻血。血液凝聚力差,一流起来不易止住,很怕人。有时夜间写作,竟致晕倒,伏在自己的一排鼻血里,第二天才被人发现。我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鼻血痕迹的手稿。他后来还常流鼻血,不过不那么厉害了。他自己知道,并不惊慌。很奇怪,他连续感冒几天,一流鼻血,感冒就好了。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,若不经意,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。《边城》一共不到七万字,他告诉我,写了半年。 他的亲戚,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“你的语言是古英语”,甚至是拉丁文。沈先生讲创作,不大爱说“结构”,他说是“组织”。我也比较喜欢“组织”这个词。“结构”过于理智,“组织”更带感情,较多作者的主观。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,用不同方法组织,看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。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。他的原稿,一改再改,天头地脚页边,都是修改的字迹,蜘蛛网似的,这里牵出一条,那里牵出一条。作品发表了,改。成书了,改。看到自己的文章,总要改。有时改了多次,反而不如原来的,以至三姐后来不许他改了(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,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)。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,最顺畅,改得最少的,只有一本《从文自传》。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,只用了三个星期,一气呵成。 在昆明的时候,我到文林街二十号他的宿舍去看他,到吃饭时总是到对西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。有时加一个西红柿,打一个鸡蛋,超不过两角五分。 他的丧事十分简单。他凡事不喜张扬,最反对搞个人的纪念活动。反对“办生做寿”。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,他死后,不开追悼会,不举行遗体告别。但火化之前,总要有一点仪式。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,是合适的。只通知少数亲友。--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。不收花圈,只有约二十多个有满鲜花的花篮,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、康乃馨、菊花、葛兰。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,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,行礼后放在遗体边。不放哀乐,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,如贝多芬的“悲怆”奏鸣曲等。沈先生面色如生,很安详地躺着。我走近他身边,看着他,久久不能离开。这样~个人,就这样地去了。我看他一眼,又看一眼,我哭了。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,种在一个精图形的小小钩赛盆里。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。这就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,沈先生喜欢的草。 (节选,有删减) 从文语录 1.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 2.我明白你会来,所以我等。 3.我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。太冷了。倘若你的眼睛这样冷,有个人的心会结成冰。 4.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,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。 阅读能够抵御时间的磨损 编辑:三河 沈从文 汪曽祺 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ercaoa.com/heccf/163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巧用藏药治肝病
- 下一篇文章: 中药每天最少学一味中药常山